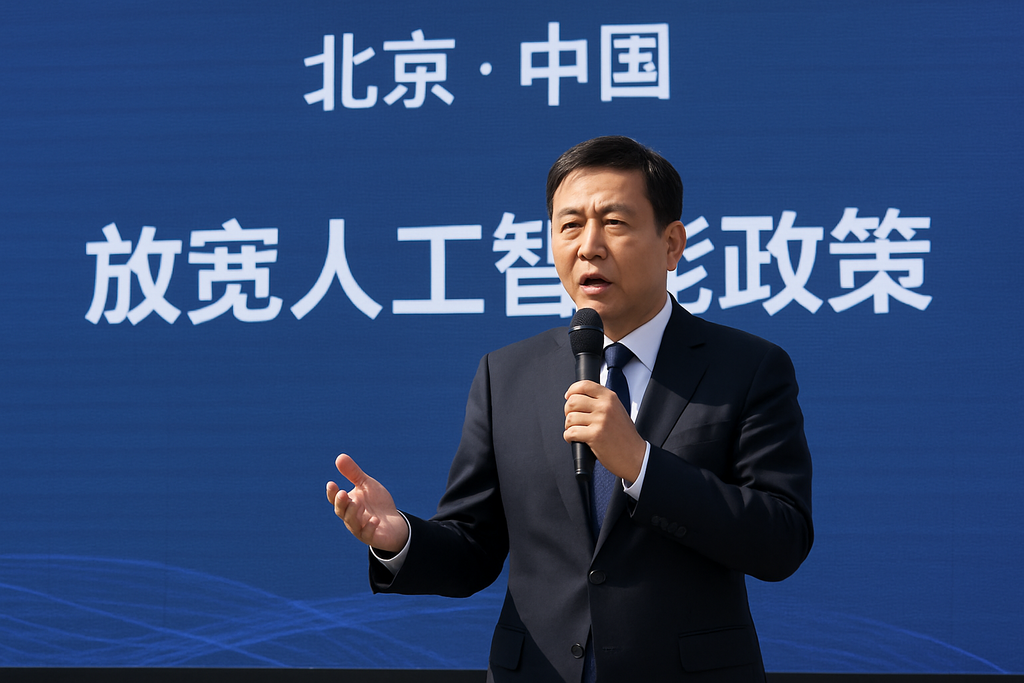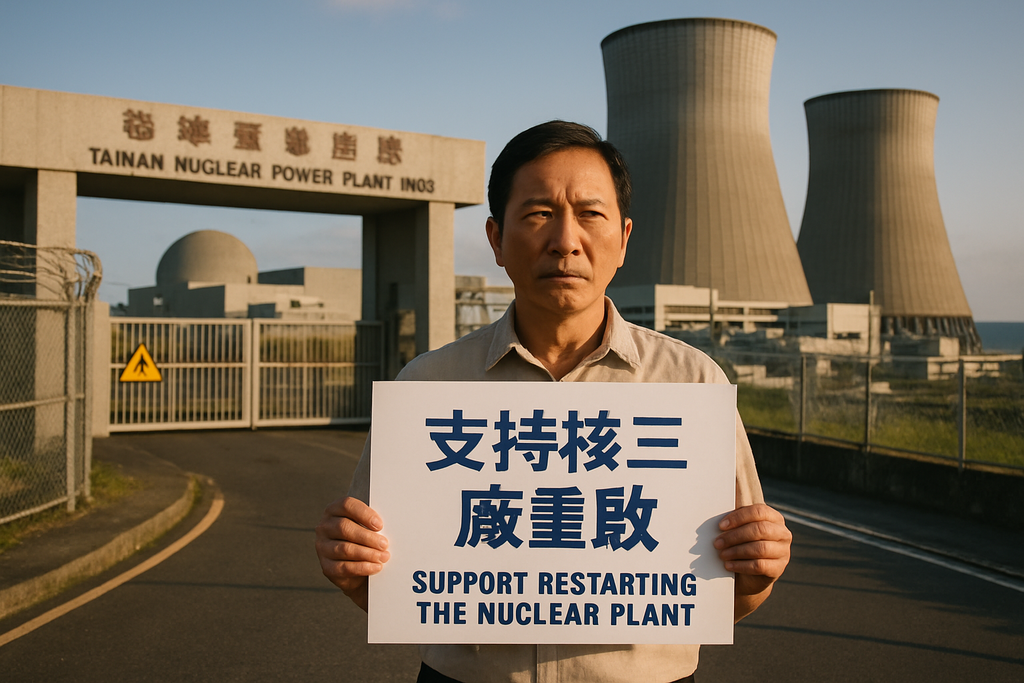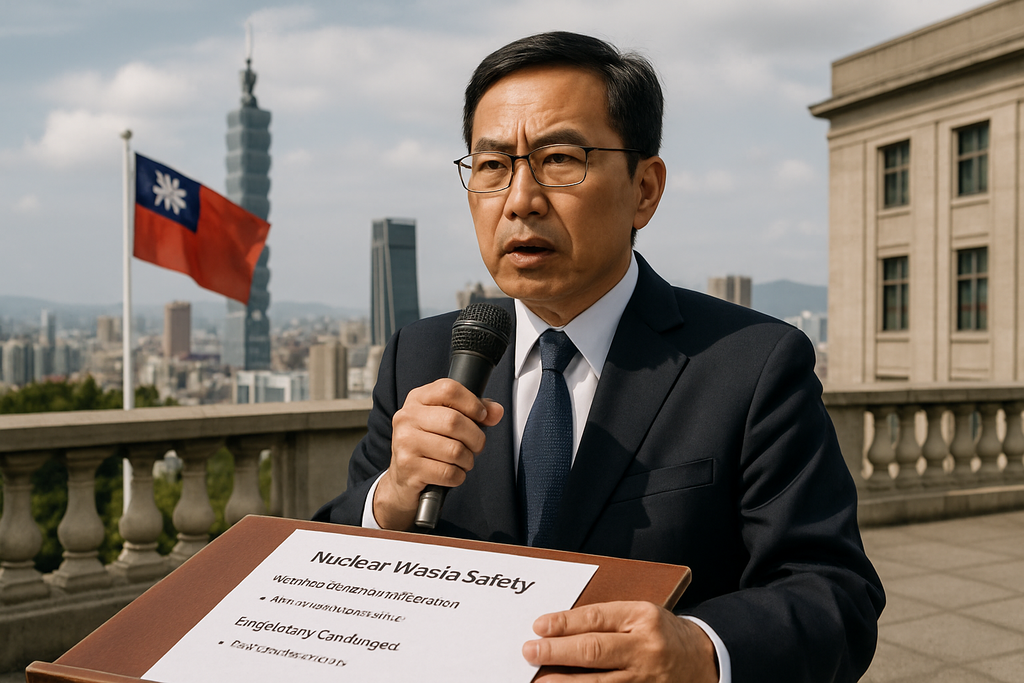
先聽聽AI怎麼看



深孔地質處置方案點燃核廢料討論新戰火
台灣的核廢料問題長年以來一直是能源政策中最棘手的爭議之一。隨著核三廠是否重啟的話題不斷延燒,高階核廢料的最終儲存方式又一次成為社會矚目的焦點。不久前,民眾黨主席黃國昌在一場公開辯論中提出「深孔地質處置」(Deep Borehole Disposal, DBD)這項新構想,立即成為議題的核心。他主張應該參照歐美地區的實作經驗,透過鑽井與地質工程,把核廢料存放在地表下三到五公里深的結晶岩層內,希望藉由多重阻隔,提高台灣核廢料最終處置的安全層級。
這套方案提出後,馬上在社會上引爆討論。贊同者強調,深孔地質處置有機會比目前暫時貯存方式更長久、更能防範地震、極端天氣或地殼運動帶來的風險;且技術已在歐美國家被認真研究,有臺灣可以參考的科學基礎。不過,反方認為台灣地質活躍、結晶岩分布有限,「要挖地底3到5公里深,根本就像在原地挖一座玉山」不切實際。此外,專家也提醒台灣的地質、水文及地下資源管理比起歐美複雜許多,若只想移植國外技術恐怕低估本土挑戰。這場主打科學論證的爭議,正好暴露出台灣社會長期知識落差與政策溝通的斷層。
民粹語言與科學討論的對撞:安全、地質與環境疑慮
深孔地質處置構想一拋出,隨即引來不少批判。反核團體、地質學界及環保組織紛紛表態質疑。環團強調,目前世界上尚無核廢料深孔方案安全運作的長期實證,芬蘭、法國等地至今也只處於試運轉階段。還有評論提到,如台灣大屯山下的岩漿庫只距地表8公里,若誤判地質結構或地熱活動,後果可能釀成本土重大災害。
台灣推動此方案也存在本地風險。例如幾乎沒大面積穩定結晶岩層,又鄰近多個活斷層、地下水豐富,加上地震頻繁,都提高了核廢料倉儲工程的難度。實際上,國際推動深孔技術的國家經常卡在社會爭議與地方阻力,芬蘭Onkalo地質處置場目前僅進入初步營運,難斷言可靠。台灣一旦貿然套用,沒有經過充分地質調查、社區溝通,非常容易導致社會信任危機。
對此,黃國昌批評反對黨及部分團體使用「民粹語言」操弄恐懼,認為應該回歸科學、理性討論。但反方認為台灣位於環太平洋地震帶,自然必須超高標準審慎以對。可以看出,雙方最大的歧異並不是技術知識,而是風險評價和社會認知落差。國際經驗也證明,深孔案場多半尚未過完整壓力測驗,安全問題其實還待長期觀察。更多相關討論可參閱「黃國昌喊往下挖『一座玉山』深放核廢料! 廢核團體發聲明打臉」。
核三重啟公投下的能源兩難與社會信任危機
這次核廢料深孔方案能燒得這麼旺,跟核三公投直接連動。台灣能源轉型進入關鍵時刻,無論是為因應電價波動、淨零碳排趨勢,還是強化供電彈性,核能再次被部分民眾視為選項。然而,只要核廢料問題懸而未決,「重啟核三」就始終過不了台灣社會信任關卡。
此次公投辯論,正反兩方一邊談能源安全與環保減碳,另一邊則直指「核廢料無處去」這道死結。正方強調只要有科學論證、技術可控,深孔地質處置就能降低風險,反方則認為核廢料的風險不應由當代人獨享,不能草率丟給未來世代。雙方所呈現的,是台灣整體能源決策中配套不足、社會參與不夠的結構問題,大家最在意的其實是「公信力」能否立得住。
如果想深入了解這場公投攻防及各方論述的深度,建議參閱「核三公投激辯4」和「核廢料埋地下『一座玉山』深?黃國昌嗆民進黨民粹式語言」。
法規、民主參與與核廢料治理的台灣困境
從制度面看,台灣其實早有核能相關法規,理論上也有核廢料管理機制與安全規範。但真實進度卻非常緩慢。原本設定要在2028年前選定最終處置場址,礙於選址曠日廢時,地方反彈與居民疑慮不斷,幾十年來幾乎沒有成果。環保團體近期主張「高放射性廢棄物選址處置條例」,要強化選址公開、資訊揭露、居民參與,不讓中央黑箱作業重演災變。
這些治理難題反映四大主因:第一,台灣社會缺少共識,容易陷入口水戰與責任推託;第二,法規與流程常在「效率」和「民主」之間拉扯,積累了深層結構病;第三,科技選項不能單靠官方推銷,必須回應本土疑慮;第四,地方自治與中央權責分工不清,造成推動綁手綁腳。對照歐洲德國、法國,都曾為核廢料立法卡關、社會抗爭持續數十年。台灣如果沒整合資訊公開、法規明確、民意參與這些要素,核廢料永遠缺一個「家」。
如對這議題有興趣,建議延伸閱讀「逾2萬束核廢料何處去?環團推『高放選址處置條例』草案,確保居民知情與參與權」。
輿論、政治語言與民眾認知:如何面對核廢料真相
在這場核廢料處置大辯論裡,媒體、政治人物怎麼形容、包裝,也深刻影響台灣人的想法。「挖一座玉山」、「深埋台北」,雖然畫面感十足,但無形間加劇焦慮與誤解。專家提醒,不論是正方還是反方,應該多用實際數據、風險評估,以及國際案例來討論,才不會落入情緒化語言的陷阱,傷害政策信任度。
其實國際案例一再證明,無論是哪一種核廢料技術,最後都脫不了透明公開、跨領域協商、持續資訊教育及民主監督這幾個關鍵。只要輿論導向和政黨攻防過頭,夾雜太多對立語言,都會讓兩邊溝通越難,消耗台灣社會寶貴的妥協與合作空間。台灣未來若想真正解決核廢料,應推動專業審查流程、建立持續對話的公民平台,讓贊成者、反對者都能把聲音講清楚,不再陷入恐核、反核或擁核的零和遊戲。
要瞭解這個議題在台灣社會的意見分歧及真實反應,可參看「【核三公投】黃國昌:核電的抽象風險是科技可控的;吳亞昕:沒人有資格為了用電把核廢風險留給下一代」。
核廢料處置的產業、科技創新與全球趨勢
隨著全球都在思考核廢料難題,這股科技創新浪潮也在台灣引起行業關注。現階段,芬蘭Onkalo處置場已進入試運轉,採用封存地底的方式等待長期壓力測試,法國的Cigéo地質處置案則計畫2027年啟用,但同樣卡在社區反彈和環境團體質疑。德國雖已廢核,仍有一千多桶廢料沒地方去;日本則靠排放福島核電廠處理水到太平洋,引發國際爭議。這些實例提醒台灣,無論哪一技術、哪種管理方式,最終都必須回應社會接受度,不能只靠科技論述。
產業技術方面,安全管理核廢料已成為高科技和半導體業界「特殊風險控管」的新焦點。像是AI監測、物聯網地質感測、再處理與包埋複合材料、地底封存與長期封裝,這些科技持續演進。另一方面,地質與水文調查能力、封存法規設計和產業鏈溝通也愈來愈重要。台灣如果想符合國際標準,不僅要強化本地地質研究、提升封存專業,更必須打造讓民意、產官學彼此監督的治理環境。
全球趨勢也指出,核廢料不只是台灣單一難題,而是所有用核電國家的世代挑戰。以芬蘭為例,安克羅(Onkalo)深地質處置場被譽為全球首例,強調利用地下深藏與多重岩層阻隔放射性,現正持續壓力測試與社區溝通。法國Cigéo則還在推動細節協商,日本福島廢水排放更成了各國政治角力焦點。從整體來看,台灣若要迎頭跟上,需要結合法制、科技、資訊安全與產業界串聯,翻轉核廢料治理瓶頸,走向新一代的安全遞進治理。
最終來講,核廢料怎麼處理,不只是科學題,也牽涉到世代正義、公共決策與社會信任。台灣當前最重要的課題,就是培養社會共識,勇敢面對核廢料現實,把科學、安全、全民參與三大基礎落實到法規、工法與討論平台,為台灣能源轉型與永續發展打下堅實基礎。